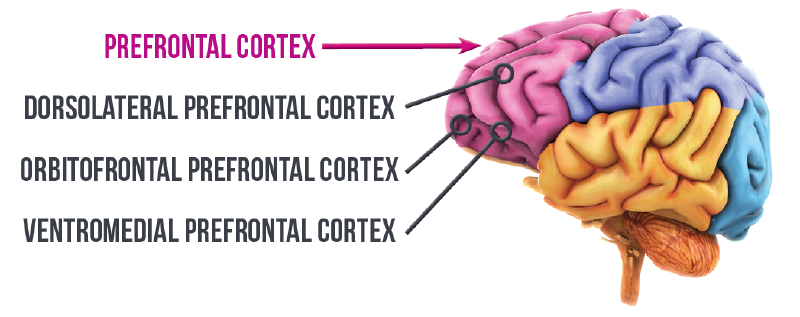我们往往对别人嗤之以鼻,却从未看清别人为什么这样。
在台湾口碑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公众对李晓明事件的态度是一种压倒性的愤怒,李晓明的律师——王赦的辩护使得乌合之众的暴怒雪上加霜——对一个事件结果的过度批评乃至关注,本身就是对真相的掩盖。这部剧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样的命题:人无自性,一人犯错,众生皆有罪。
未审视过的即是遥远。以正义之名,乘愤怒之势,借司法之理仓促判决一个犯人死刑,无助于发现真相,无助于让未来变得更好,更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正如李大芝面对新闻媒体所哭诉的那样:你们杀的人比我哥还多。那些拿着相机,亦或是坐在办公桌前计算收视率的人,又何尝不是凶手的变体?
认为程序正义优于结果正义,这一点上,王赦是一个尝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人。所有人,哪怕他的至亲,都认为他不过是在为杀人犯,社会的渣滓辩护。所有人,特别是被害者家属,都只关注他们遭遇悲剧的可能和遭遇的悲剧本身,至于别人遭遇的悲剧他们充耳不闻。他们更无法想象的是,施害人的家属和他们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点的人往往拿出这样的反事实陈辞(counterfactual proposition):如果你的家人被这样杀害,你知道会有什么感受吗?事实上,王赦遵循自己做事的因果逻辑——因为有人杀人,所以他必须去辩护,争取探究真相的机会,而非否定后件的演绎逻辑——你感受不到这些痛苦是因为李晓明并没有杀害你的家人。他们又往往是高声宣扬人性本恶,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根除恶人。这种观点的可笑之处在于,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就完全可以找出判断恶人的方法,并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休谟说,任何事物本身既然不高贵也不卑贱,事物的特征来自人类情感的特性与构造。当怀疑主义发挥到极致,所谓的“自我”并不存在笛卡尔那样的基础主义的回答,所谓的“我”,所谓的“善恶”,无非是一堆经验片段的集合而已,并没有一个独立于经验的,实在的“我”。“我”与“善恶”的形成受制于后天的经历与环境。应景的是,在每一集的开头,画面都会给到一个具体的网络评论,以及在它下方不断上升的点赞数——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不过是一句评论。王赦深知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他的付出并不是宽恕李晓明,他也不是在挑战法律与道德,而是为了还法律以尊严——让未来更好。
以上只是引子。不过思路和今天要说的自控力与瘾癖(也是自己在大数据院的研究项目)有关。
现有自控力(self-control)理论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回顾一下经典的自控力理论。第一种理论是discounting model of impulsiveness (Ainslie, 1975). 这种理论融合了决策,认为自控力体现在面对一个small but sooner和一个larger but later的奖励时克制自身的冲动选择后者。比如给小孩子不同量和延时的棉花糖。第二种是冷热系统理论,在“do if it makes sense”和“do if it feels good”之间权衡。第三种是self-regulatory strength model, 也称作ego-depletion,把自控力看作是有限资源。
我们可以对其共性做出两点归纳:其一,理论关注的是给定刺激物,在一个时间点下考察被试的选择。比如最有名的棉花糖实验;其二,成瘾往往意味着自控力低下或者自控力资源消耗导致了在目标环境中对诱惑的屈从。比如ego depletion的一个实验,为两组饥饿的被试提供萝卜,甜点,但其中的实验组被要求只能吃萝卜,控制组吃甜点。之后,让两组被试都尝试解决一个无解的几何题目,考察他们坚持的时间。其中的理论在于,要求吃萝卜的实验组需要消耗一定的自控力资源去抵抗更有吸引力的甜点,因此他们在后续的任务中会更快地放弃。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尽管结果支持了假设,但是该实验流程显然是有问题的。第一,实验组是被要求的,违背了一些高IF自控力综述对自控力的定义(self-initiated);第二点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萝卜与甜点具有不同的升糖指数(食物转化为血糖的速度),因此在把葡萄糖作为自控力资源指标的前提下,吃不同的食物这一过程引入了混淆变量。
那么这上述理论的两点归纳体现出什么问题?第一点注重即时的选择,并没有探讨这种情景的形成。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完全不涉及自控力特质的情况下将自身引入有引诱物或者可能引起自身冲动的环境;第二点问题,这些理论似乎把自控当作了一种类似免疫系统的东西,人们总是会采用自控,只不过很多情况是自控资源不足,或者自控进程没有启动。接下来要说的是,在讨论成瘾的范畴时,这个前提恰恰值得怀疑。
本书开头引用了罗恩的案例——为什么罗恩不得不在下午五点之前完成那份表格的时候,他愤怒至极?与此同时,他的同事们也要填写相同的表格,为什么只有罗恩会勃然大怒呢?事实上,罗恩的怒火还进一步转化成了接下来的行为动机。在简单的抱怨之后,罗恩拿起电话,告诉妻子说今晚会回去很晚——尽管他5点就可以完成表格了。这时,他在心里已经默默规划好了,下班后在回家路上的酒店喝上一杯。
完成表格与决定下班后喝酒看似两件毫无联系的事情在此时却毫无征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尝试用经典自控力理论去解释一下。首先,在罗恩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在“努力完成工作”和“下班后去喝一杯”两者中做抉择。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是自控的,因为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无法避免他下班后去酒馆。其次,这个决定是在他克制自己的冲动、平静下来去完成工作之前,此时自控力资源没有消耗。注意,strength model中自控力能量的消耗是建立在行动之上的,如果仅仅是一个做事的念头就能消耗,就谈不上一种“资源”了。因此合理的推测是ego depletion并没有发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即生活的“核心冲突”。
罗恩7岁时,有一天他在自己房间里听到了父母的争吵,这种事经常发生,他却无能为力。
随后,吵架声停了,母亲走到他房间里来,要求他把客厅收拾一下,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客人。
“可是妈妈,我的乐高城堡才搭了半截。”“我真的非常需要你现在为我做这些,我头疼。”母亲的语气是如此不容置喙,“罗恩,我现在就要你去。”当罗恩收拾完毕准备回到房间时,却又被父亲喊住,让罗恩代替他去遛狗。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恩的母亲好像越来越需要他的帮助,而父亲也变得愈来愈容易激动。没有人关注过他的需求,这就是他的成长环境。他一直努力地迎合父母,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求得到他们的关注,却最终带着伤痕成长起来。
罗恩不会发现的是,他成为了束缚自己的那张网的一部分。二十年后,他依然“沿用”了这一人际关系模式,尽管他对漠视自己的需求表现得相当愤怒,但他隐隐约约在控制着自己不要惹乱子,要让老板和会计部分负责人这对“新父母”高兴。
罗恩的冲突在于,采用实际的解决方案,为自己的需求发声和避免提出过多要求以求相安无事时间的矛盾。他的无助和愤怒是自己造成的,为了找回生活的控制感,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一定会在这个矛盾之外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瘾,往往是一种自我设限。
从罗恩的案例可以看出,成瘾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涉及感情的问题。成瘾本身属于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说替代,因为它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情感),也因为它不在一个层面解决问题(在事情之外)。这种解决方案寻求的是一种生活的控制感,这种控制感和自控力也并无实际关系。白天高度自控的人未必就是牢牢把握了幸福和生活控制感的人,成瘾的人也可能高度自控,经常忍受延迟。
比如996工作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性熬夜。不遗巨细的工作环境吞噬了所有人留给自己的时间,去个性化的集体环境也磨平了心灵的向度。压抑的必会重返,从这一点看,熬夜玩手机,和酗酒,抽烟,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是这个时代诉求控制感的一剂药方。
那么自控力与成瘾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自控力(特指dispositional self-control)并不影响成瘾的质变点,而仅仅影响成瘾的量变。举一个自己宿舍的例子。A,B,C三位室友都喜欢打游戏。结局是A挂科,但BC不挂科,BC之间有成绩差异。先说A君,挂科是因为打游戏有限度最高,临考复习期间也无法克制自己。他潜意识认为打游戏是必须做的事情,不与其他事情的优先度做严格划分。这种情况下自控力预测成瘾与挂科与否无效。对于B君,打游戏或看直播时间次多,但不挂科,因为他有优先度规划,即最重要事情做完或者接近做完才能打游戏。这种时候自控力是有效的,因为主体同时面对一个SS(smaller, sooner reward)和LL(larger but later reward)选择,符合自控力实验的经典范式。C君则是下自习后固定时间打游戏,更像是一种习惯,而习惯被认为是一种无意识自控力,因此这种情况下自控力也是有效的。当然更重要的在于,BC两人打游戏的内因是不涉及情感驱动的。
这里要明确两对概念,生理上瘾与心理上瘾,习惯与成瘾。
生理学认为,成瘾是一种慢性脑病,即多巴胺受体变化以及表观遗传变异。生理病变导致了自控的失效。但是对美军越战吸毒士兵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点,他们在回国戒毒后不再复发,与本土美国人表现出巨大差异。这个差异的源头,就是是否有情感因素驱动。军人只是生理上瘾,需要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临时需要一种处理情感问题的方法,一旦这个情感因素消失,瘾癖就可以根除。同理,如果打游戏并不是一种情感需求(例如一定要和朋友一起玩,或者在游戏中称兄道弟),并不构成上瘾。玩游戏的时间也不能作为成瘾与否的界定标准。
另外,习惯与成瘾也需要明确区分。改变习惯比改变成瘾更难,因为后者应对的是复杂而强烈的情感问题。习惯和瘾癖的区分就在于需要看这种行为是否是紧随被侮辱,被忽视,感到绝望等情况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会主动放弃自控。
对与自控力不涉及成瘾质变点的论述,可以用以下两个思想实验论证。
第一,假定strength model成立,即自控力是一种有限资源,那么人们在学习时总会有手机,电脑,网络等诱惑,那么随着学习时间的延长,自控力资源总会消耗殆尽,其结果就是最后人人都会屈从诱惑。
第二,给定一个没有诱惑的环境,由于人们不需要消耗自控力资源抵制诱惑,那么最后便不会有人成瘾,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由于劳累而不学习。然而事实是许多中学学生依旧会翻出学校的围墙,去网吧等环境。即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环境。
最后要说的是对研究自控力和成瘾的一些启示。
如果想用机器学习预测成瘾,就不能单纯地考量自控力,而是需要同时思考情绪,无助感和生活的控制感。同时成瘾前涉及到很多个体差异较大的变量也可以尝试归纳,如一个人的防御模式。其次要对与成瘾相关的混淆概念(如习惯)要有区分,保证选择的feature要能体现出其差异,即有效度。